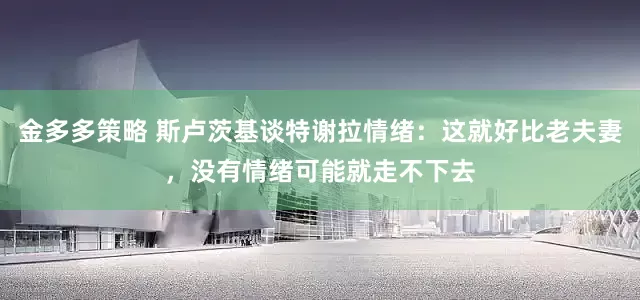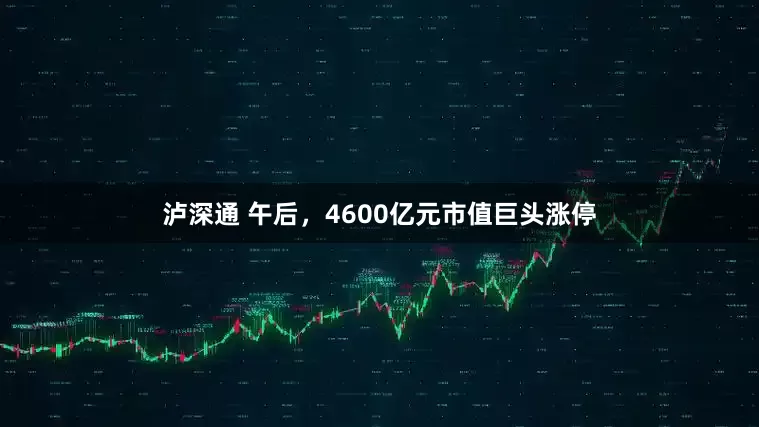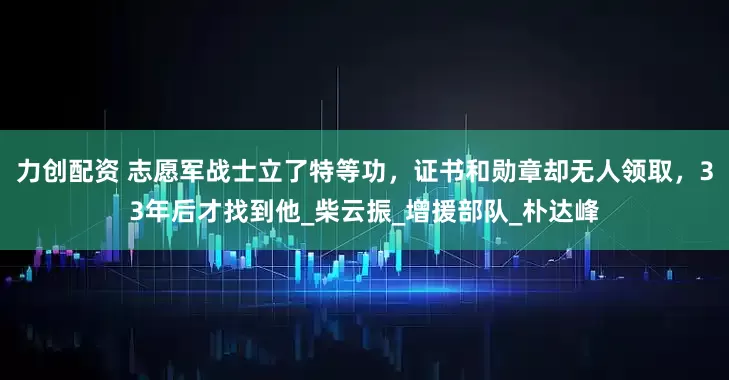
1984年秋天,在湖北孝感的一处军营大门口力创配资,一位来自四川的农民缓缓撩起他那花白的头发,露出了头顶上宛如蜈蚣爬行般排列的24道伤疤;随后,他又伸出右手,只见那断了一截的食指格外显眼。
就在这时,一名警卫员急匆匆地跑进军部大楼,高声喊道:“老班长找到了!”整个军营顿时沸腾了起来——那个曾被朝鲜官方画成“遗像”供奉了整整33年的“烈士”,竟然活生生地站在了阳光下。
朴达峰上的“最后一人”:24道伤疤背后的故事
1951年5月的朴达峰,硝烟弥漫,炮火连天,山岩被燃烧得焦黑一片。志愿军十五军阵地前,美军第25师像潮水般蜂拥而至。22岁的班长柴云振带领着仅剩的三名战友,顶着密集的炮火冲进敌群。他们用短短20分钟时间夺回了三个重要山头,炸毁了敌方的指挥所。弹药耗尽后,他们凭着顽强的意志拼刺刀肉搏。当最后一名战友倒下,柴云振孤身一人面对四名美军。他奋力击毙三人,随后与最后一名敌人翻滚进入战壕——右手的食指被敌人咬断,随后对方还抓起石块狠狠砸向他的头颅,令他头破血流。
展开剩余77%增援部队抵达时,战场上只剩下奄奄一息的柴云振。他全身布满24处伤口,军服被鲜血浸透,右手食指仅剩半截。彭德怀亲自致电军长秦基伟称赞:“十五军展示了钢铁般的战斗力!”此次战斗歼灭敌人两百余人力创配资,守住了前线指挥部,为志愿军北移赢得了关键的战略时间。战后,志愿军总部授予柴云振“特等功臣”和“一级战斗英雄”荣誉,但这些证书和勋章却一直无人领取。
三等残废证和千斤粮票:英雄归乡的艰难路
1952年4月,在包头医院,头部缠满厚厚绷带的柴云振接过了三等乙级残废军人证书以及500公斤的粮票复员费,踏上了返乡之路。部队曾派人寻找他,但由于战地医院转移时档案丢失,只知道他的名字是“柴云振”(其实是文书误记,他的本名是柴云正)。回到四川岳池县大佛乡后,他从未向乡亲们提起自己的战功。女儿柴昌英回忆说:“剃头师傅多收了他两分钱,因为他头上的伤疤太多,剃起来很难受。”有人劝他去部队找工作,他却摇头说:“手指断了,不能再参军了,不能再给国家添麻烦。”
与此同时,在朝鲜平壤的军事博物馆里,挂起了他的“遗像”,与黄继光、邱少云等英雄并列;在上甘岭战役中,战友们高喊着“向柴云振学习”冲锋杀敌。而真正的柴云振,则赤脚在田间插秧,后来担任乡长,依然住在简陋的土房里,用残缺的手握紧锄头,辛勤开垦荒地。
启事上的名字错误:拖拉机旁命运的转折
1984年9月,在岳池县的一个加油站,柴兵荣刚加完煤油,无意间瞥见了《四川日报》角落的一则寻人启事:“寻战斗英雄柴云振,朴达峰阻击战功臣……”虽然名字中的“振”字与父亲本名“云正”不符,但其他细节完全吻合。他立刻奔回家,却被柴云振拒绝了,老人推开报纸说:“全国有多少同名同姓的,不能冒领别人的荣誉!”儿子卖掉家中的年猪,凑足了路费,硬拉着父亲登上了开往湖北的绿皮火车。
在军营里,曾在警卫连任文书的董贵成含泪解释:当年因听到四川口音,将“云正”误记成了“云振”。老战友孙洪发颤抖着掀开柴云振的头发,仔细数着那24处伤疤,泪流满面。得知消息的秦基伟连夜发来电报:“三十三年寻找,终于迎回了英雄!”
朝鲜的“遗像”:金日成亲自授勋的访朝之行
1985年10月,平壤锦绣山议事堂内,金日成将“一级自由独立勋章”亲手佩戴在柴云振胸前:“您活着回来了,这是奇迹,中朝两国人民永远感谢您!”在军事博物馆里,柴云振驻足于挂着他“烈士”遗像的展柜前,画像下方写着“烈士柴云振”。他亲自取下这幅画像,带回家中,成为最珍贵的“烈士证明”。
归国后,县政府曾安排他住房,但他婉言谢绝:“我家有瓦房遮风挡雨,已经够好了。”在担任省政协委员期间,他共提交了200多份提案,最为执着的是为村里修建道路。村民们回忆:“他拄着拐杖多次跑县城,终于让水泥路修成,这条路后来被命名为‘英雄路’,路碑旁还种满了他从朝鲜带回来的松树。”
最后的军礼:空降兵部队的精神传承
2018年寒冬,在岳池县殡仪馆内,六名身穿制服的空降兵战士向柴云振的灵柩敬礼。他们都是“上甘岭特功八连”的现役官兵——正是当年柴云振所在的连队。现任连长毛小龙说道:“老班长是我们连队的灵魂,他‘隐功报国’的精神早已写进了我们的连队训词。”
送别当天,孙女柴萍将一枚弹壳轻轻放在爷爷的掌心。这是柴云振从朴达峰带回的弹壳,曾伴随着他讲述那些峥嵘岁月的故事:“真正的英雄,早已留在朝鲜战场上了,我算什么?”如今,柴家四代人从军:两个儿子守卫边疆,孙女柴萍成为空降兵,曾孙女于2021年入伍。家族相册中,不同年代穿着军装的身影力创配资,永远站立在那条被命名为“英雄路”的乡村小路上。
发布于:天津市翔云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